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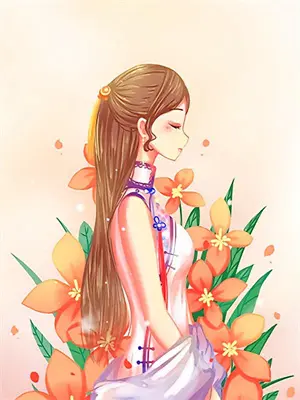
言情小说连载
言情小说《晓雾渐浓主角分别是沈砚之苏寒作者“Asz祈乐”创作纯净无弹窗版阅读体验极剧情简介如下:第一章——突变暮春夜间的雨总带着股化不开的寒打在青灰色的瓦檐上簌簌作沈砚之收伞竹骨轻颤着抖落一串水恰好溅在廊下那双云纹锦靴她抬眼便撞进一双古井似的眸那人倚着朱漆廊玄色劲装外罩了件月白披被雨雾洇得半湿的发梢垂在颊倒衬得下颌线愈发冷腰间悬着柄乌鞘短刀穗上系着枚青铜铃是江南听雪楼特有的标沈楼主倒是稀对方先开了声音像浸过寒潭的冰寒山堂的地...
主角:沈砚之,苏寒江 更新:2025-11-07 22:27:27
扫描二维码手机上阅读
第一章——突变暮春夜间的雨总带着股化不开的寒意,打在青灰色的瓦檐上簌簌作响。
沈砚之收伞时,竹骨轻颤着抖落一串水珠,恰好溅在廊下那双云纹锦靴边。
她抬眼便撞进一双古井似的眸子。那人倚着朱漆廊柱,玄色劲装外罩了件月白披风,
被雨雾洇得半湿的发梢垂在颊边,倒衬得下颌线愈发冷硬。腰间悬着柄乌鞘短刀,
刀穗上系着枚青铜铃铛,是江南听雪楼特有的标记。沈楼主倒是稀客。
对方先开了口,声音像浸过寒潭的冰棱,寒山堂的地界,不欢迎藏头露尾的角色。
沈砚之将伞柄在石阶上顿了顿,浅青色的裙摆扫过潮湿的地面。
她今日换了身寻常书生的长衫,若非袖口不经意露出的银线绣纹,倒真像个避雨的过客。
苏堂主说笑了,她指尖摩挲着伞柄上的缠绳,听闻苏堂主近日得了幅《寒江独钓图》,
特来一观。苏寒江挑眉时,眉上的疤痕微微动了动。那是三年前在漠北留下的,
据说当时她单枪匹马挑了整个黑风寨,刀光里滚出来的名声,比寒山堂的匾额还要响亮。
沈楼主消息灵通,她直起身时,披风下摆扫过廊柱,带起一阵清冽的冷香,只是这画,
概不外借。雨势忽然大了,檐角的水流成了线。沈砚之望着庭院里被打残的芭蕉叶,
忽然轻笑一声:若是我说,我知道画中渔翁的真实身份呢?
苏寒江的手几不可察地按在了刀柄上。那幅画是她从一个垂死的密探手里接过的,
画轴夹层里藏着朝廷与北狄私通的密信,她追查了三月,却始终解不开画中隐藏的暗号。
沈楼主有话不妨直说。苏寒江的声音沉了沉,披风下的手已经握住了刀柄,
青铜铃铛在寂静中轻轻晃了晃,却没发出半点声响。沈砚之转身望向雨幕,
长衫的衣摆被风掀起一角。三日前,洛阳城破,守将林啸战死。她的声音很轻,
像雨丝落在水面,但我在城郊破庙,见过一个断了左臂的渔翁。苏寒江猛地抬头,
披风上的水珠簌簌坠落。林啸正是三年前与她一同镇守漠北的将领,后来被诬陷通敌,
满门抄斩,唯独他本人不知所踪。他在哪?她的声音里带了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握刀的指节泛白。我可以带你去找他。沈砚之转过头,雨丝落在她睫毛上,
像覆了层薄霜,但我有条件。远处传来更夫打更的声音,咚地一声敲在暮色里。
苏寒江看着眼前这个素未谋面的女子,她的眼神平静得像深潭,却藏着让人无法拒绝的力量。
什么条件?沈砚之抬手,将被雨打湿的鬓发别到耳后,露出一截纤细的脖颈。
我要听雪楼与寒山堂,暂时联手。风卷着雨丝穿过回廊,吹得廊下的灯笼左右摇晃。
苏寒江盯着她袖口的银线绣纹——那是用西域冰蚕丝绣成的寒梅,只有听雪楼主沈砚之,
才会用这样奢侈的绣线。传闻中,这位沈楼主年纪轻轻便执掌江南第一情报组织,手段狠戾,
从不露面。却没人知道,她左手心有块月牙形的疤痕,
那是十年前在街头被恶犬咬伤时留下的。就像没人知道,
苏寒江每晚都会对着一幅褪色的帕子发呆,帕子上绣着半朵山茶,另一半,
在林啸失踪时弄丢了。好。苏寒江松开刀柄,青铜铃铛终于轻轻响了一声,明日卯时,
城门外老槐树下见。沈砚之颔首,转身踏入雨幕。
浅青色的身影很快被浓得化不开的暮色吞没,只留下一串渐行渐远的脚步声,混在雨声里,
渐渐模糊。苏寒江站在廊下,望着她消失的方向,直到灯笼里的烛火燃尽最后一寸。
她抬手抚上眼角的疤痕,那里还残留着漠北风沙的粗糙感。雨还在下,
敲打着寒山堂的每一寸瓦当,像谁在低声诉说着陈年旧事。
第二章——谜底卯时的天色尚未破晓,墨蓝的天幕上还悬着几颗疏星。
城门外的老槐树早已抽出新绿,晨露顺着卷曲的嫩叶滑落,在青石板上洇出点点湿痕。
沈砚之到时,苏寒江已倚在树身等了片刻。她换了身便于行动的灰布短打,
玄色披风叠成方巾系在腰间,乌鞘短刀依旧悬在腰侧,只是刀穗上的青铜铃铛被黑布裹了,
想来是怕行路时发出声响。“倒比我早。”沈砚之将手中的油纸包递过去,
“城南铺子的热糕,还温着。”苏寒江瞥了眼那油纸包,没接。“林啸的事,不宜耽搁。
”沈砚之也不勉强,收回手时指尖触到包底的余温,倒像是自己掌心的热度。“随我来。
”她转身往城郊方向走,浅青色的长衫在晨雾里若隐若现,“他藏在破庙时,
总在破晓前去溪边取水。”两人一前一后走在田埂上,露水打湿了裤脚,带着春草的清腥气。
苏寒江的脚步很轻,落地时几乎听不见声响,沈砚之却能从身后那道若有若无的视线里,
察觉到对方始终保持着三尺距离——那是江湖人对峙时最安全的间距。“听雪楼的消息网,
连林啸断了左臂都知道?”苏寒江忽然开口,打破了一路的寂静。
沈砚之踩着田埂边缘的枯草,声音被晨雾滤得有些发飘:“去年冬月,
有个货郎在洛阳城外捡到只断手,指节上有常年握枪留下的厚茧,掌心还嵌着半枚旧箭簇。
”她顿了顿,侧过脸看她,“那箭簇的形制,是漠北军专用的。”苏寒江的脚步猛地顿住,
披风下的手又攥紧了刀柄。她认得那箭簇——三年前漠北那场混战,林啸为了护她,
左臂挨了北狄一箭,箭头断在骨缝里,军医说这辈子都取不出来了。“货郎在哪?
”她的声音里带着冰碴。“病死了。”沈砚之转过身,晨露落在她的发间,像撒了把碎银,
“临死前把那截断手埋在了老槐树下,说等林将军回来,好给他凑全了身子。
”苏寒江望着远处薄雾笼罩的村庄,喉间发紧。她想起当年林啸总笑她心硬,
说战场杀敌时眼睛都不眨,却见不得路边饿死的野狗。那时她总骂他妇人之仁,如今才懂,
有些柔软是藏在骨头缝里的,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示人。“到了。
”沈砚之忽然停在一道山涧前。溪水潺潺,水底的卵石上还沾着新鲜的泥痕,
“顺着水往上走,第三个山洞就是。”苏寒江没动,忽然转头看她:“你为何要帮我?
”沈砚之低头拨弄着腰间的玉佩,那玉佩是块暖玉,被她常年摩挲得温润剔透。
“听雪楼要查朝廷通敌的证据,林啸是关键。”她的声音很淡,“而你,
是唯一能让他开口的人。”苏寒江盯着她的眼睛,那双眸子在晨雾里显得格外清亮,
却像蒙着层纱,看不真切。她忽然想起三年前漠北的那个雪夜,她中了埋伏,
眼看就要被乱箭穿心,是个穿着浅青色衣裙的女子忽然从雪地里窜出来,
用一把银匕挑落了所有箭矢。那时她只记得对方手心有块月牙形的疤痕,
转身消失在风雪里时,发间还别着朵干枯的山茶。“你认识山茶吗?”苏寒江忽然问。
沈砚之的手指顿了顿,玉佩上的温度仿佛骤然变冷。“知道。”她抬眼时,
睫毛上的露水落了下来,“江南的山茶,开得比北方早。”苏寒江没再追问,转身跃过山涧。
她的轻功极好,像只掠水的燕子,转瞬便消失在密林里。沈砚之望着她的背影,
缓缓松开紧握的玉佩,掌心的月牙形疤痕在晨光里泛着淡淡的红。她其实没说,
那个病死的货郎,是她的远房表哥。当年林啸满门抄斩,是表哥偷偷把他藏在柴房,
断手也是为了让他躲过追兵,硬生生自己砍下来的。表哥临死前拉着她的手,
说寒山堂的苏堂主心善,让她务必把消息递到。山洞里阴暗潮湿,角落里堆着些干草,
空气中弥漫着草药和霉味。苏寒江刚走进洞,就看到角落里缩着个蓬头垢面的人影,
左臂空荡荡的袖子随风摆动。“林啸?”她的声音发颤。那人猛地抬头,
露出张布满疤痕的脸。看到苏寒江的瞬间,他浑浊的眼睛里爆发出光亮,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却因为腿上的伤重重摔倒在地。“苏……苏堂主……”苏寒江冲过去扶住他,
指尖触到他身上的骨头,才发现他已经瘦得脱了形。“你怎么弄成这样?
”“他们一直在找我……”林啸咳得厉害,咳出的痰里带着血丝,
“密信……密信被我缝在了画轴里……本想送到寒山堂,
却被北狄的人截了……”“画轴我拿到了。”苏寒江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
里面正是那幅《寒江独钓图》,“但暗号解不开。”林啸接过画轴,
枯瘦的手指抚过画面上的渔翁。“渔翁的鱼竿……是北斗七星的方位……”他喘着气,
指腹点在鱼竿的七个节点上,
“每个节点对应一个字……连起来是……是……”他的话没说完,
洞口忽然传来一阵衣袂破风的声响。苏寒江猛地转身,刀已出鞘,
寒光在昏暗的山洞里一闪而过。三个黑衣人不知何时站在洞口,
为首的那人脸上带着道十字形的疤痕,手里握着柄沾血的长刀。“苏堂主,好久不见。
”疤痕脸笑起来时,脸上的肉拧成一团,“北狄王说了,只要交出林啸和密信,饶你不死。
”“黑风寨的余孽。”苏寒江的声音冷得像冰,“三年前没斩草除根,倒是我的疏忽。
”疤痕脸的眼神狠了起来:“当年你挑了我们寨子,杀了我大哥,这笔账,今日该算了!
”他挥刀便砍,刀锋带着凌厉的风声。苏寒江侧身避开,短刀直刺对方心口。
她的刀法狠辣干脆,招招直击要害,显然是在生死场里磨砺出来的。但对方人多,
且个个身手不弱,她护着林啸,渐渐有些吃力。就在这时,
一道浅青色的身影忽然从洞顶落下,银匕划破空气,精准地刺穿了一个黑衣人的咽喉。
沈砚之落在苏寒江身侧,手腕翻转,银匕上的血珠滴落在地,
与她浅色的衣衫形成刺目的对比。“你怎么来了?”苏寒江有些意外。“听雪楼的事,
没办完。”沈砚之的声音里带着喘息,显然是一路追过来的,“别分心。”两人背靠背站着,
苏寒江的短刀大开大合,沈砚之的银匕则刁钻诡异,一刚一柔,竟像是演练过千百遍般默契。
疤痕脸渐渐不敌,虚晃一招便想逃跑,却被沈砚之的银匕缠住手腕,
苏寒江的短刀趁机从他后心刺入。黑衣人很快被解决干净,山洞里只剩下浓重的血腥味。
林啸看着地上的尸体,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咳着咳着,竟呕出一口黑血。“林啸!
”苏寒江连忙扶住他,却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变冷。“密信……”林啸抓住她的手,
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在……在画轴夹层……交给……交给信任的人……”他的目光转向沈砚之,似乎想说什么,
最终却只化作一声轻咳,头歪在苏寒江怀里,没了声息。山洞里静得可怕,
只有洞外的溪水还在潺潺流淌。苏寒江抱着林啸冰冷的身体,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只有紧握的刀柄在微微颤抖。沈砚之默默地走到洞口,背对着她站着。晨光已经穿透薄雾,
照在她浅青色的衣衫上,仿佛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边。
“他说的信任的人……”苏寒江忽然开口,声音沙哑得厉害,“是你吗?”沈砚之没回头,
只望着远处渐渐亮起的天空。“我会帮你把密信交给该交的人。
”苏寒江低头看着怀里的林啸,忽然摸到他怀里有个硬硬的东西。掏出来一看,
是块褪色的帕子,上面绣着半朵山茶,针脚粗糙,却看得出来绣时用了心。另一半山茶,
在她自己的枕下压了三年。她忽然想起刚才沈砚之拨弄玉佩时,袖口滑落的瞬间,
手腕内侧似乎有个极淡的印记,像朵没开全的山茶。“沈砚之。”她抬头时,眼眶有些发红,
“十年前,西街口被恶犬追的小姑娘,是你吗?”沈砚之的肩膀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
晨风吹起她的发,露出耳后那截细腻的肌肤,那里有个浅浅的牙印,
是当年被恶犬咬伤时留下的。“那天扔给你半块糕的人。”苏寒江的声音里带着哽咽,
“是我。”沈砚之缓缓转过身,晨光落在她的脸上,那双总是蒙着层纱的眼睛,
此刻清亮得像山涧的溪水。“我知道。”她轻声说,“你当时把帕子撕了一半给我擦血,
上面绣着山茶。”风从洞口吹进来,卷起地上的灰尘,迷了人的眼。
苏寒江望着她手心的月牙形疤痕,忽然想起三年前漠北雪夜里那个救了她的女子,
发间别着的那朵干枯的山茶,原来不是幻觉。原来有些人,兜兜转转,
总会在某个清晨或黄昏,重新遇见。沈砚之走过来,轻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心很暖,
恰好熨贴了苏寒江冰凉的指尖。“密信的事,我们一起办。”苏寒江看着她眼里的光,
忽然点了点头。阳光穿过洞口,照在两人交握的手上,仿佛要把那些陈年的风霜,
都晒得暖起来。远处的村庄升起了炊烟,混着晨雾和青草的气息,在山谷里慢慢散开。
第三章——新生林啸的尸身被葬在山洞后的竹林里,没有墓碑,只在坟前插了根削尖的竹片,
上面刻着个歪歪扭扭的“林”字。苏寒江用短刀掘土时,指节被碎石磨破,
血珠滴在新翻的泥土里,很快晕开一小片暗红。沈砚之站在竹林边缘,
看着她沉默地填土、压实,动作利落得像在处理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直到最后一捧土落下,
苏寒江才直起身,对着那堆新土静立片刻,忽然从怀里掏出那半块绣着山茶的帕子,
轻轻放在坟前。“他总说,等战事平息,就去江南看山茶。”她的声音很轻,被风吹得散碎,
“说那里的花开得比漠北的雪还要烈。”沈砚之走过去,将一方干净的帕子递到她面前。
“江南的山茶,清明前后就该谢了。”她顿了顿,补充道,“但后山有种野茶,能开到五月。
”苏寒江接过帕子,指尖触到布料上细密的针脚,是听雪楼特有的云锦织法。
她忽然想起沈砚之耳后的牙印,想起十年前那个雪天,
自己把刚买的桂花糕掰了一半扔给巷子里缩着的小姑娘,
转身时衣角扫过对方冻得通红的脸颊,触到一块凹凸不平的疤痕。“画轴呢?”她收起帕子,
声音恢复了平日的冷硬。沈砚之从袖中取出那幅《寒江独钓图》,
画轴边缘已被血水浸得发皱。“林啸说鱼竿是北斗七星的方位,
我们得找个能看清星象的地方。”两人顺着山涧往回走时,日头已升到半空。晨雾散尽,
露出连绵的青山,溪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的光,倒映着两道并肩而行的身影。
苏寒江忽然发现,沈砚之走路时总习惯性地靠左,脚步轻得像踩在云絮上,
唯有在经过陡峭处时,才会下意识地伸手扶一把身边的岩石,指腹在粗糙的石壁上短暂停留,
留下浅淡的白痕。“听雪楼的人,都像你这样?”苏寒江踢开脚边的石子,石子滚进溪水里,
溅起一串水花。“什么样?”沈砚之侧身避开横生的树枝,浅青色的衣袖扫过崖边的野蔷薇,
带起几片花瓣。“神出鬼没,还……”苏寒江顿了顿,没说下去。她其实想说,
还总藏着些不肯示人的柔软,像此刻落在沈砚之发间的蔷薇花瓣,明明带着尖刺,
偏要缀上点粉白的温柔。沈砚之却像是懂了,忽然停下脚步,转身看向她。
阳光穿过她的发梢,在脸颊上投下细碎的光斑,眼角那点平日里不易察觉的暖意,
此刻竟看得真切。“听雪楼有个哑仆,总在我窗台上摆着晒干的山茶。”她忽然说,
“他说当年在漠北战场,是个穿灰布短打的姑娘救了他,那姑娘腰间的刀穗上,
系着枚青铜铃铛。”苏寒江的脚步猛地顿住,腰间的短刀似乎也跟着发烫。
她想起三年前黑风寨那场混战,自己确实救过个被绑在柱子上的少年,
当时他嗓子被毒烟熏坏,说不出话,只死死攥着她递过去的水囊,指节泛白。“他现在在哪?
”她的声音有些发紧。“在江南养伤。”沈砚之弯腰捡起片落在地上的蔷薇花瓣,
花瓣的边缘已经有些枯卷,“他说等能开口了,就去学唱江南的小调,唱给救命恩人听。
网友评论
小编推荐
最新小说
最新资讯
最新评论